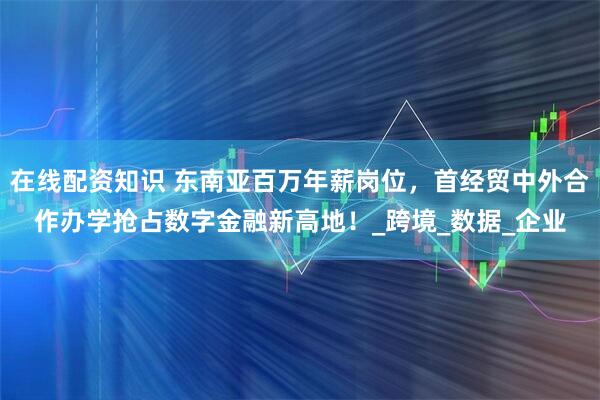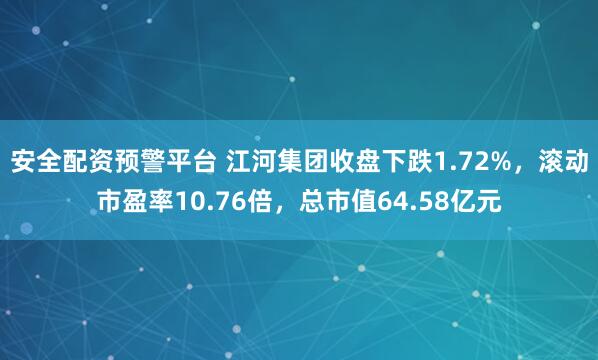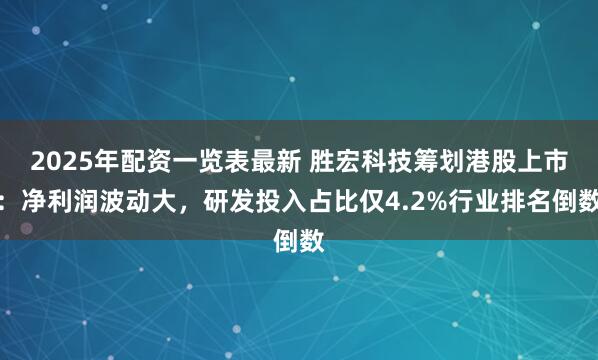苏州传世名著系列
浣纱记
前言
苏州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,文化积淀深厚,历史上创造了一座又一座文化高峰,在中华文化史上做出了杰出贡献。以人文荟萃著称的苏州,历代文人众多,著述卷帙浩繁。这些著述内容丰富、论题广泛,享誉中外,堪称中国文化经典。本系列文章以苏州传世名著为主题,展现苏州丰厚渊博的历史文化典籍,发挥经典名著在全民阅读中的引领作用,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鲜活起来,成为涵养当代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资源。
《浣纱记》
借古抒怀
《浣纱记》是由明代昆山文人梁辰鱼所作昆剧,取材自吴越争霸时期,两国的兴衰变幻。剧中以范蠡西施的离合为主线,二人初识于苎萝溪畔,一见如故,彼时西施正临水浣纱,便以之赠范蠡定情,剧名也由此而来。后因越国战败,西施被作为计策献给吴王,助越灭吴后,二人最终相携归隐江湖。作为一部讲述吴越两国重大战争历史的剧目,《浣纱记》选择了越国大夫范蠡作为视角切入,与作者梁辰鱼个人的经历与情怀或有某种隐秘关联。
梁辰鱼铜像
梁辰鱼大概生于明正德十五年(1520),祖籍中州(今河南),先祖梁元德赴任昆山知州,因而举家搬迁至此。到了梁辰鱼这代,家中尚算殷实,他对于科考仕途不甚挂心,终日沉迷诗词音律。但作为长子,梁辰鱼背负着家族的殷殷期盼,因而仍一直参加乡试,以图有机会博取功名。
明代的科举已逐渐僵化,与社会现实脱节。“好任侠,风流自赏,放荡不羁”的梁辰鱼或许未必不明白出题者的意图,只是无法违背自己的心意作答。在他看来,当时明廷面临内忧外患,外有倭寇连年侵袭东南沿海,内有严党把持朝政,苛税重赋,民不聊生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空谈修身养性,似乎于国事无补,因而他在父亲去世后,便不再寄望于科考。
◁《青园图卷》局部(明·沈周绘)▷
嘉靖四十一年(1562),时任闽浙总督的胡宗宪在东南沿海剿倭,偶然听闻梁辰鱼其人,便寄信邀其前往杭州入幕。崇尚“侠气”的梁辰鱼从内心欣赏胡宗宪这样能力卓越,肯办实事的官员,因而对于此次邀约满怀期待。然而天不遂人愿,就在梁辰鱼奔赴杭州的途中,胡宗宪却因严党倒台受到牵连入狱。无奈折返的梁辰鱼,心中愤懑可想而知。对于他而言,最失望的或许并非不能入幕一展宏图,而是连胡宗宪这样一位为国为民做实事的官员也要被党争牵连迫害,足以说明明廷内部已然衰朽不堪。
《西子浣纱图》(五代·周文矩绘)
这时的梁辰鱼虽然功名无成,但也小有才名,思想上也逐渐成熟。他感慨于朝廷的黑暗,希望写一部好作品,抒写胸中块垒,产生了以吴越争霸的历史描写当世之事的念头。他的叙事技巧也非常纯熟巧妙,不从宏观历史出发,而是以范蠡和西施的爱情为切入点,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。这部作品问世后,一时各大戏班都争相演出。
昆腔新声
◁《西湖十景图卷》局部( 清·董邦达绘)▷
《浣纱记》被后世认为是第一部将昆腔新声——“水磨调”推上戏剧舞台的作品。所谓“水磨调”,是由魏良辅等人在保留南戏柔美婉转风格的基础上,融入北曲的慷慨激昂,改良而成的新昆腔。
我国的戏曲发源很早,至宋元时期达到一个高峰。当时北方在宋杂剧、金院本、诸宫调以及民间说唱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较为成熟的体系——元杂剧(或称北曲)。差不多同一时期,在南方江浙一带也产生了以唐宋大曲、宋词、宋杂剧等为基础的戏曲形式,称“南戏”。明代文人王世贞在《艺苑卮言》中曾评价,南北二曲,“譬之同一师承,而顿渐分教;俱为国臣,而文武异科。”即是说北曲南戏是同一源流下发展出的不同分支,二者风格截然不同。明代戏曲家徐渭在《南词叙录》中言:“今之北曲,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,壮伟狠戾,武夫马上之歌。”北曲节奏铿锵有力,而南戏往往流丽婉转,一字多音。对于这一点,王世贞进行了更为简洁的总结:“凡曲,北字多而调促,促处见筋;南字少而调缓,缓处见眼。”(《曲藻》)并认为:“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;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”,即北曲擅长叙事,而南戏更重抒情。
《度曲须知》(明·沈宠绥著)明崇祯十二年刻本
魏良辅将北曲南戏的优点结合,形成了“北曲南唱”的新昆腔。明代沈宠绥形容昆腔:“拍挨冷板,弦索苍凉,启口轻圆,收音纯细,一字之长延之数息,余音委婉绕梁。”但由于魏良辅并无剧作之才2025年配资一览表最新,因而“水磨调”一开始多用于清唱。期间也有一些剧作家尝试将其搬上舞台,但并未引起轰动。到萌发《浣纱记》灵感,梁辰鱼的技艺和思想均已准备充分,为了以更好的形式呈现,他细致研究魏良辅度曲之法,力图将《浣纱记》打磨成符合心中艺术理想的作品。魏良辅擅长音律,在乐器搭配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,使之更适合“水磨调”的特性。梁辰鱼擅长剧本创作,但音律方面未必都能合韵,因而他在写曲辞时,尤为注意,力求一字一句都能符合昆腔新声的格律。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下,最终成就了这部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佳作——《浣纱记》。
发布于:北京市力创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